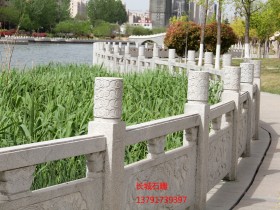- A+
政邦茶座>>
近期,梁衡先生的散文集《人生谁能无补丁》刚一出版,便受到了广泛关注,还被评为“政邦推荐·2023年度好书”。与此同时,继《觅渡》《洗尘》之后,随着他的散文集《重阳》的出版,“梁衡散文三部曲”宣告完成,其被形容为“以50年的亲身经历为纵坐标,以这期间的大事、大情、大理为横坐标,展现了一个记者、学者、官员的所见与所思” 。
我与梁衡先生是多年老友,我们一直计划做一期政邦茶座,从夏天到秋天期间,出现了各种意外情况,最终能够成行的时候,才发觉意外竟也是一种巧合。
在新作里,梁衡先生写道,岁月蹉跎,命运多舛,人生中谁能没有补丁,老树即便不废也会发新芽,风雨过后总归是晴天,他为何会提出“补丁哲学”,这对人生而言意味着什么?
本期政邦茶座,与梁衡先生共同聊聊文学,谈谈人生。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是梁衡,他是著名散文家,是学者,是新闻理论家,是科普作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是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普首席人文顾问。他曾任《光明日报》记者,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有新闻四部曲,分别是《记者札记》《评委笔记》《署长笔记》《总编手记》,还著有散文集,包括《觅渡》《洗尘》《重阳》《树梢上的中国》《把栏杆拍遍》《千秋人物》,以及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有《梁衡文集》九卷、《梁衡文存》三卷。曾获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杂文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先后有60多篇次文章入选大、中、小学教材,这些文章包括《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壶口瀑布》《夏感》《青山不老》《把栏杆拍遍》等 。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表示,说起来咱们相识已有20年,我始终在关注您的散文创作。您在新闻、文学、政治等诸多方面都颇有成就,然而给许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当年入选教材的《晋祠》,它影响了众多人。您怎样看待自己的创作历程呢?
梁衡:

如果简单梳理一下,2022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两个“整年”。其中一个“整年”是,我参加新闻工作满50年了。我于1972年正式调到《内蒙古日报》,并拿到了记者证。当然,在1970年以前,我在地方的新闻宣传部通讯组工作。那时通讯组的主要工作也是写稿子 。当时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办报依靠群众来稿,还有基层通讯员组织 。1972年正式调入报社,到前年恰好是50年。1982年开始,也就是10年之后,我的一篇文章《晋祠》入选课本,到前年刚好是40年,这是另一个“整年”。
所以,前年是两个“整年”,我进入新闻工作50年,入选人教社全国教材40年,并且是连续40年不断,很多作家一生可能都未必能有一篇入选,这是我的幸运。40年一直未变,中间有落选情况,比如《晋祠》是最早入选的,后来换了,换成我写的《壶口瀑布》,还有《夏感》《居里夫人》《青山不老》等 。有人做过统计,若按照入选篇次来计算,大概有70篇左右。其中有一段时期,我们的教材编选放宽了限制,各出版社能够自行编选教材 。
高明勇表示确实是这样 。三年前 ,他围绕对方的散文创作史写了一篇长论 ,名为《文章传统的传承与进阶——论梁衡的兼及其散文创作史》 。长论里提到 ,经过数十年的创作探索与实践 ,“梁衡散文”正在成为一种“梁衡现象” 。一方面 ,“梁衡散文”被大量选入各类教材 。另一方面 ,“梁衡散文”频繁出现在包括高考 、中考在内的各种考试中 。在当代作家当中,在教材里能占据如此长的时间,能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供学生当作范文来阅读,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剖析的现象。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文集,按照年龄来考量,您那时应该算是出版文集的作者里最为年轻的吧?大概主要还是教育工作者居多?
梁衡:
没错,确实算是比较年轻的。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作者出版文集,在印象里似乎没出过几个。是三个人或者四个人,并且都是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的那些长者,比如叶圣陶先生,他们都曾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做出过贡献 。
高明勇:那时候您还没退休就已经出文集了,什么原因?
梁衡:
我现在回想起来也纳闷,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下的这个决心。
图为2007年梁衡先生(左)与政邦智库理事长高明勇在一起。

高明勇表示,这里还涉及另外一件事,他在来的途中突然想到,大家关注对方,除了关注其在文学、新闻方面的表现外,实际上还有一个方面是其在教育上的价值。不管是语文教育,还是新闻教育,对方都做了很多工作。然而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那本“文集”出版得早,后来写的诸多文章未能被选入 。
梁衡:
他们如今依旧常常提及这件事,还讨论是否要进行修订。当时出版了九卷,如今估计不止十五卷。说起此事,自1982年《晋祠》发表并入选课本起,直至我创作瞿秋白(《觅渡,觅渡,渡何处》),在1996年发表《觅渡》之前,这一阶段基本以描写山水为主。因为身为记者,需要四处奔波,从而有机会接触各地的山水。我上学的时候,中学课本里有《小石谭记》,它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说到这里,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文革”期间我们的山水散文出现了转变,是以“杨朔模式”呈现的。恰好这个时期刚打倒“四人帮”,尽管我曾是杨朔的忠实粉丝,但我是全国第一个公开批判“杨朔模式”的。见1982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当前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要是给自己的创作史划分界限,这第一段可算作“山水散文”,曾经,我也觉得“山水散文”就是我创作散文的巅峰了,就到这儿为止了,那时很多人也认为我只是个写“山水散文”的 。所以,中国作协为我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冯牧副主席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他在会上对我批判“杨朔模式”予以肯定,那应当是第一个阶段,是“山水散文”创作阶段的高峰 。
高明勇:这是一个分水岭,之后您的创作就转向了。
梁衡:
其实很多事情并非自己所规划,事不由人,主要是后来随着社会发展,机构发生变革,我被调任到新闻出版署,如此一来,我接触的面大大拓宽,创作不再仅是山水,特别是人文方面的创作也多了起来。
高明勇:客观上,事业的平台带来的眼界变化也不一样。
梁衡:
当时党史开始有一些解密,像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这样的大事,一些资料能够看到,当时《中华儿女》杂志发表周恩来相关文章最多,专访了不少当事人,所以我写周恩来时,调来刊物的合订本,摞起来比我的办公桌还高,就这样查阅了不少资料,里面有大量当事人回忆。这就是1998年完成的《大无大有周恩来》。

高明勇表示,这篇文章让他印象深刻,他第一次看到是在2002年,也就是22年前,当时他正在《中国教育报》实习,晚上寄宿在北大,挤在同学的宿舍里。那时他自己没有电脑,需要用时就借用其他同学的,结果意外发现不少同学的电脑桌面上都有这篇文章的文档。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您,对您的了解也不多,看到众多北大同学的电脑里都存有这篇文章,便打开阅读,结果一下子就被打动了。虽说之前读过他的传记,可觉得这样一篇文章把栏杆拍遍 梁衡,用“无”和“有”两个字把周恩来的一生写得极为透彻 。
梁衡:
记得写那篇文章时,我刚开始学习打字,用的是286电脑,速度很慢,有个部下帮我打字,他边打边问,梁署长,这篇文章敢不敢发呀 。
高明勇表示,这个细节颇具趣味,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撰写关于“伟人”的文章或书籍时,史学家也好,文学家也罢,查阅资料时会碰到信息公开程度方面的问题,写作时会遭遇相关人物事件阐释权口径方面的问题,发表时会面临身份与话语权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去写“伟人”或政治人物 。如果您当时不具备那个身份,说实话即便能够想到,即便能够写出来,也不一定能够发出来。
梁衡:
是的 随后我进入了“政治散文”创作时期 季羡林先生给我的散文起名为“政治散文” 这是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持续了很长时间 后来创作内容不光有“政治散文” 还有“历史人物散文” 我写过辛弃疾 李清照等历史人物 。到了2000年,我调到人民日报的那一年,发表了写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第二年发表了写李清照的《乱世中的美神》。如果这些算一个阶段,那就是第三个阶段,如果不算,归在“政治散文”的人物散文里面,就都算第二个阶段。这也就是你所说的不断的“转型” 。
高明勇:除去这些特殊的遭遇,您创作“政治散文”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梁衡:
其实,我对“政治散文”中的人物散文创作,有着强烈的针对性,也有着强烈的批判性,我没把这些给别人公开讲过,当然,这也是因为没有人来和我探讨这个问题。
有一回给报社记者授课,那时有部很热门的电视剧《亮剑》,其中有句台词是“每一个将军都有一个假想敌” 。我讲道,“每一个将军都有个假想敌,每一篇文章都应当有个真靶子” 。你身为写评论的人是清楚的,肯定要思索你的“真靶子”究竟是谁,究竟是社会上的哪一种现象,或者哪一类人、哪一类事 。写评论是这样,写消息也是这样,写通讯同样如此。写消息时要明确针对的是什么,写通讯时也要清楚针对的是什么。所以我的文章起码得做到这一点,即每一篇都得有一个“真靶子” 。
就说我第二个阶段进行“政治散文”创作,这与“山水散文”有很大不同,笔下的人物都是具体针对的一个个对象,我写的时候都带有悲剧情节,我都是选取这个人物的社会意义所在,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毁灭”,鲁迅讲过“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句话出自鲁迅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因为被“毁灭”,所以这个人物才被人看到,所以才有可能感动人 。

高明勇表示,他曾问询身边朋友对其散文的看法,在“政治散文”领域,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中,除了刚才提到的《大无大有周恩来》,还有写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这两篇也是公认影响力极大的 。
梁衡:
写这两篇有着特别的现实背景 ,社会上曾有段时间流行一些官员利用职权 ,借写回忆录为自己树碑立传 ,粉饰自己的历史 ,为此当时中央专门发了一个文件限制官员出自传 ,针对这种风气 ,我写了瞿秋白 ,突出他的坦白 ,人格的坦白 ,正因为有针对性 ,所以才会打动很多人的心 ,大家心照不宣 ,觉得就是在批评社会上那种不好风气 。当然,瞿秋白自身非常伟大,他的这种品格能够照耀到我们,直至如今仍在发挥作用,已然超越了普通政治人物 。
我有时与他人聊天,有时在某些场合讲课,期间会提及您所写的瞿秋白,三次前往常州寻觅素材令人感慨,三个假设式的“如果”同样让人感慨,特别是“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这句话,更是令人动容,正因如此,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读完文章后潸然泪下,想要与您相见,对于这样一位曾身处高位的政治人物,如何进行写作,实际上就是如何进行评价的问题。对作家而言,这个评价并非冷冰冰的政治评价、历史评价,更多的是要将其还原成一个人。就拿您早些年的“山水散文”来说,我一直在思索,您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真的仅仅是山山水水吗?很多时候,写的是隐匿在山水背后的人,这些人既有同时代人的审美情趣,又有写作者本人的审美价值。写政治人物,其实也是在写人,首先要让政治人物走下圣坛,走下神坛,使其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 。写历史人物,说白了就是把他们从历史的迷雾里请出来 。
梁衡:
写作要让人能够记住,写周恩来,呼应了当时一种隐隐约约的社会情绪,大家都说不出来,但谁心里都知道,为周恩来的“大无”、为他的委屈感到不公,这首先是对“四人帮”的批判,也有对毛泽东的批评,当时不敢说有多少批判成分,至少是有反思在里面的,所以这篇文章引起轰动在情理之中 。包括后来写的《假如毛泽东去骑马》,都是有深刻反思的。
就个人阅读体验而言,《假如毛泽东去骑马》这篇文章,我觉得它的价值起码不低于写瞿秋白的文章以及写周恩来的文章。前段时间,一些地方邀请我去讲如何调研,我还拿出这篇文章与大家分享。我说毛泽东是大家公认的擅长调研的人,然而这篇文章开拓了新的途径,从别的角度来阐述调研的重要意义,要是无法做好调研,即便你是擅长调研的人,同样有可能在决策方面出现问题。
梁衡:
这的确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他连警卫排都已准备妥当,还为他挑选了一匹白马,其颜色与陕北的马相同,已到这般地步,然而因战争,出现了那么一点差错,便错开了一个时代,一切就此改变。
高明勇表示,这篇文章影响力不大,不过他个人很喜欢。他还说,有人讲历史不能假设,实际上反向思考问题,反而能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另外,这篇文章有不少场景化的细节描写,并且一些情节符合戏剧理论中的“冲突”,照这样都能够拍成影视剧了 。
梁衡:

这或许是我创作散文的一个特性。有人已与我取得联系,准备改编剧本。此外,还要补充一点,根据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改编的电影《觅渡》已然上映了。
刚才提到了第二阶段,2000年我调到人民日报工作,此后我陆续写了党史人物张闻天把栏杆拍遍 梁衡,作品是《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愈见光辉的灵魂》,退休后我还写了彭德怀,作品是《带伤的重阳木》,政治人物就这样一路写下来了。
如果把“政治散文”看作是三十岁以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那么第三个“转型”便是《树梢上的中国》。说起《树梢上的中国》,它与我的工作变动有关。我在2006年退居二线进入全国人大。到人大后,因历史的阴差阳错,我被分到了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到了农委之后,接触到了农业方面诸多事情,因林业归农口,便有了这个机遇,2012年堪称一个转折,这一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古树的文章,标题为《一棵抱炸弹的老樟树》,江西有棵老樟树曾救了毛泽东一命,战争时期,一个炸弹落下挂在树上,未爆炸,树下正是毛泽东居住的房子 。
这一年全国人大农业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局进行了一次座谈,我询问资源司长,“你负责管理什么?”她回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活立木的积蓄量。”我又说:“只负责管理活立木有多少立方,那树上承载的文化由谁来管?黄帝陵上有名的柏树,每年都有人去祭拜,这由谁来管?”那个司长表示:“确实没人管,也没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原本是做记者的,也就是所谓的杂家,对各种事物都怀有兴趣,恰好当下有空闲时间了,于是我说:“我来负责管理”。
高明勇:相当于一个“三不管”带来的灵感。
梁衡:
对,是“三不管”。后来,在调查过程中,我渐渐悟出一个新的概念,即“人文森林”。我打算学做“人文森林学”,一开始,我真的是先写论文,就是附在《树梢上的中国》后面的那一篇。2012年6月27日,我在全国第六届中国生态文化高峰论坛上,发表了这篇名为《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的论文。还表示要在中国找出100棵有文化底蕴的古树,如今看来,这根本办不到了,要晓得挖掘一棵古树的文化内涵,就如同进行一次历史研究和田野考古工作。撰写一棵树常常需要来回奔波数千公里,要采访三四次,耗费好几年时间。如今我快80岁了,要写一百棵古树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现在看到《树梢上的中国》收录的仅有33棵 。2013年7月2日,有关于创立“人文森林学”的建议在《中国绿色时报》发表。
从山水散文不断转型为政治散文,再到人文森林散文,你能看出,并非是我按照计划去写什么,而是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形势迫使我去写什么。就如同鲁迅所说,这是一种遵命文学,是遵从时代的命运。(未完待续)
- 我的微信
- 这是我的微信扫一扫
-

- 我的微信公众号
- 我的微信公众号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