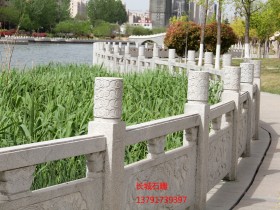- A+
7月10日,北京地铁官方发布信息,自2018年开始,计划逐步移除车站内部的硬质分流隔离栏。进入今年6月,再度对车站内的隔离栏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削减了不必要的隔离设施。到目前为止,已累计拆除隔离栏长达12280米。
新京报的记者在北京的多座地铁站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自从围栏被拆除后,站内的空间变得更加开阔。大多数乘客都觉得障碍物减少了,通行变得更加便捷。尤其是在客流量高峰的时候,一些地铁站已经开始使用可伸缩的移动围栏来替换之前的固定围栏。
李迪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副教授,指出北京地铁的这一举措具有积极影响,决策者和管理者展现出对民众需求的关注,而物理围栏的移除也有利于培养公众的边界意识。
7月13日,在四惠东站的一号线与八通线换乘大厅,那曾经存在的金属围栏已被移除,使得整个大厅显得更加开阔明亮。摄影: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现场1 四惠东站
换乘大厅拆“围栏笼”更舒适
近期,众多乘客注意到,在地铁一号线四惠东站进行换乘时,原本的平台大厅内不见了那道高逾一米八的金属围栏,使得空间显得更为开阔。在过去大约十年间,此处一直设有这样的围栏,仿佛为大厅搭建了一个“围栏笼”。
7月13日,居住在通州的陈先生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在早高峰时段进行换乘,乘客们必须依次排队,沿着曲折的“S”形线路往返行走,高峰期甚至需跟随前人步行约五分钟,方可抵达一号线站台。

陈先生习惯乘坐地铁上下班,他对这种做法表示认同护栏与栏杆的区别,认为设置围栏有积极作用,能有效防止人们插队和翻越围栏走捷径。“然而,这样的围栏确实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陈先生往常习惯于在交通高峰时段出行,然而,某次他推着童车在非高峰时间出行时,却意外发现乘坐并不便捷,“人虽不多,却不得不绕过铁栅栏,这才意识到绕行的路途颇为曲折。”陈先生感慨道,自从栏杆被拆除,原本需要步行几分钟的换乘路程,现在只需20多米即可到达,大大方便了出行。
马女士认为之前的围栏仿佛是囚笼,将乘客围困其中。如今围栏已被移除,她觉得这就像是获得了“自由”,“对于大多数上班族而言,排队等候已成为常态,实在无需如此高大的围栏来限制他们。”
7月13日傍晚六时左右,正值交通高峰时段,四惠东站内人潮涌动,新京报记者观察到,由于缺乏栏杆的阻隔,乘客们能够便捷地完成换乘,大家有序地排队等候,并未引发任何拥堵现象。
芍药居地铁站内,在乘客稀少时段,那可灵活调整长度的围栏被安置在了紧邻墙壁的一侧。摄影:新京报的郑新洽。
现场2 芍药居站
移动拉伸围栏代替固定围栏 更灵活
芍药居地铁站亦是一个客流量大的换乘枢纽。该站负责连接10号线与13号线的换乘工作。在此之前,两线换乘通道的出口处设置了一道长达六十多米、高约一米多的金属围栏,将站厅的一侧与站台分隔开来。当乘客从13号线方向进入10号线站厅后,他们不能直接下到站台,而是必须通过一条“S”形通道护栏与栏杆的区别,绕行大约近百米的距离。
7月13日,新京报记者从10号线芍药居站了解到,班长定寅硕表示,采取绕行措施旨在早晚高峰时段合理推迟乘客抵达站台的时间,以减轻车辆尚未进站时站台上的客流压力。

非高峰时期,围栏显得不那么亲切,迫使乘客不得不选择更长的绕行路径。经过对站台整体状况的全面考量,以及充分的论证分析,为了向乘客提供更为便捷的换乘选择,芍药居站决定将围栏移除的方案提交给公司,该方案在经过评估后得到了批准。
定寅硕指出,鉴于疫情当前,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人数有所下降;在围栏被移除的一个月期间,无论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站台并未观察到人群聚集的现象。
疫情结束后,预计在客流高峰时段仍需实施一定的流量控制,为此,他们已经预先制定了应对计划。在站厅的墙壁附近,设置了两个合计长度达到8米的可伸缩金属隔离栏,这些围栏底部配备了滚轮。
在地铁芍药居站,临近大客流高峰时段之前,地铁员工启动了可伸缩移动护栏,对进站乘客进行有序分流。这一场景,由新京报的记者郑新洽先生进行了拍摄记录。
定寅硕及数名员工向新京报记者展示,在人流密集时段,他们能在短短半分钟内迅速将围栏移动至指定位置,并展开至25米之长。高峰期结束后,围栏随即被收回,紧靠墙壁竖立,站厅恢复畅通无阻的通行环境。
新京报记者观察到,这种可移动和可拉伸的围栏在高度和宽度上与以往使用的固定金属围栏相差无几。定寅硕补充道,当使用这种围栏时,会有专人负责监护,以确保乘客不会随意移动。
地铁内的限流设施全部集中堆放在站点的某一角落。由新京报的记者马明仁拍摄。
现场3四惠站

迷宫一样的“围栏阵”拆了 更敞亮
7月14日,新京报记者在四惠地铁站观察到,原先设置在地铁一号线与八通线出入口交汇处的限流设施已全部被移除,目前仅剩下用于区分已安检区域与未安检区域的隔离围栏仍在使用,而那些被撤除的护栏则被统一堆放在车站的一隅。
在此前,当乘客经过该站点时,他们必须绕行那道由S型固定路线构成的“围栏阵”来完成换乘。如今,隔离护栏已被移除,乘客现在可以轻松地在一线和八通线之间完成换乘。一线地铁的入口都位于四惠站的北侧,而八通线的入口则位于南侧,这使得乘客的换乘过程变得极其便捷。
新京报的记者经过实测发现,乘客在车辆停靠后只需走过十多块地砖,便能抵达换乘线路的地下入口,这样的换乘过程仅需不到一分钟,即可完成两站之间的转换。
张先生向记者透露,昔日于四惠站换乘颇为不便,一则是因为限流栏限定的通行路径拉长了行程,且限流栏之间的距离仅能容许两人并肩同行,而在客流高峰时段,乘客间的无意碰撞往往会引发争执;再则,由于原有的限流栏既高又密集,使得视线受到误导,不熟悉路线的乘客难以辨别哪条路径可实现换乘,感觉就像置身于迷宫之中。
在天通苑南站,高峰时段并未采取限制人流的措施,相反,他们选择了开启侧门,以便乘客能更快捷地离开车站。这一场景由新京报的记者马明仁拍摄记录。
现场4 天通苑南站
早晚高峰区别对待 更便捷
14日18时20分,新京报记者来到天通苑南站站口,尽管正值晚高峰时段,但该地铁站的乘客数量却相对较少。站口位于限流区域,但侧门已对外开放,方便乘客出入,而限流区域的中心区域并未被封闭。

张女士每日需在五道口与天通苑南站之间来回奔波,她表示,天通苑南地铁站在早晨的高峰时段乘客众多,而到了晚上,由于该站并非换乘枢纽,乘客数量相对较少。特别是这里的居民中,有很多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他们频繁的加班使得该地铁站的客流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分散。
刘先生另一位乘客也表示,在清晨时分,天通苑南地铁站依旧会采取人流控制措施,"这里无疑是北京早高峰的标志性地点"。然而,对于这一限流措施,刘先生保持中立立场,"一方面,我认为这是必要的,限流有助于保障安全并管理客流;另一方面,由于通道狭窄,这无疑给乘客的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
刘先生指出,鉴于天通苑南站位于高架桥之上,其候车区域的空间相对有限,面对客流高峰时段,采取在站外进行人流控制的措施,是合乎常理的做法。
北京地铁:软质导流带增大乘客行走空间
新京报记者通过长城石雕得知,自2018年起,该拆除栅栏的行动便已启动。考虑到车站的具体情况和客流变化,非必需的围栏得到了削减。截至目前,车站内硬质导流围栏已被整理和检查,总长度达到了20008米。在此过程中,共拆除了12280米的导流围栏,其中3730米被更换为软质导流带,此举显著提升了乘客的通行空间。
北京地铁相关部门表示,过往岁月里,地铁站内外设置的导流围栏在确保乘车秩序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起到了隔离和指引的双重功能。但伴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升,这些导流围栏的设置需求正逐渐减少。为了更好地服务乘客、提升通行速度以及改善车站环境,长城石雕等设施正逐步被撤除,以减少部分导流围栏。
北京地铁还透露,未来将根据客流量动态调整导流围栏的布局,并计划逐步更换5296米的导流围栏,同时推广使用可伸缩的推拉式导流围栏。此外,还将配合施划导行线等替代手段,旨在提升乘客的遵守秩序的意识。
芍药居地铁站,在客流高峰期间,启用了可调节长度的移动围栏设施。该场景由新京报的郑新洽记者进行拍摄。
专家:决策管理者要“眼里有人”

李迪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副教授兼代理院长,于7月14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决策者和管理者应当关注人心,他们应当坚持以人为核心,将人作为中心。
李迪华回忆起自己在北京西客站下车后的那段经历,他发现,尽管目的地地铁安检口就在不远的对面,他却不得不拖着行李绕一大圈,走了许久才抵达。他觉得,这种护栏隔离的做法只是针对特定时间段管理乘客的一种手段,然而在非高峰时段,它却给乘客们带来了不便。
李迪华指出,北京的诸多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已增设护栏,旨在遏制违规停车现象。然而,此举却对道路的使用效率及公众出行带来了不利影响。他认为,违规停车理应受到法律和执法人员的双重约束,而不应牺牲其他公共资源的利益。
李迪华指出,目前北京地铁正在进行导流围栏的拆除工作,这其中包括自去年起对时政道路隔离围栏的移除,这些举措象征着一种进步与变革,理应受到认可,并为其他公共领域管理提供借鉴。
李迪华提出,在拆除护栏的过程中,必须加强管理措施。对于客流量大的地铁站,若需进行客流疏导,可增派管理人员,或者采用张贴指引标识、铺设地面指示线等方法来指引乘客正确行进。
李迪华认为,采用物理隔离是最简便的管理手段,有助于明确责任范围,节省人力和精力,然而,这种方法并不利于培养公共秩序参与者的行为规范。
李迪华指出,拆除围栏这一行为旨在告知公众,我们应当逐渐养成依据公共秩序来设定界限的习惯,并在此基础上自觉维护这些界限,而非仅仅依赖实体障碍物来实现规范。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马明仁
校对 李世辉
- 我的微信
- 这是我的微信扫一扫
-

- 我的微信公众号
- 我的微信公众号扫一扫
-